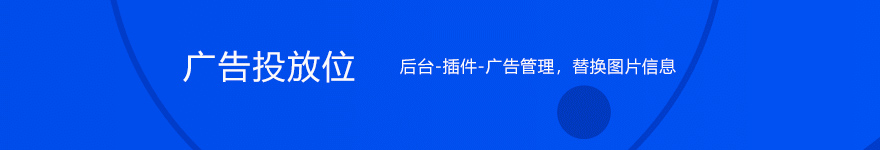來源:《財經》
雖然歐美多家銀行已被收購,但這并不意味著歐美銀行業風暴偃旗息鼓,監管者對于金融機構的風控援手,將帶來一連串的外溢效應——家庭和企業貸款收緊、外貿商品與服務需求壓抑、股票和其他資產價格下降??

圖/ic
文 |《財經》記者 康愷 特派記者 金焱 發自華盛頓
編輯|袁滿
15年前的危情似乎正在重演,金融投資者們環顧四周,警覺地探尋著下一個倒下的金融機構會是誰。利率高企、經濟衰退陰霾下,歐美銀行業倒閉、收購的戲碼再次上演,這次會不一樣嗎?
當地時間3月19日,瑞士聯邦政府的一紙公告,宣告了瑞士信貸銀行(下稱“瑞信”)167年獨立經營的終結。該公告使歐洲最大的金融集團得以變得更為龐大——瑞士聯合銀行集團(UBS,下稱“瑞銀”)以四折的價格收購了瑞信。根據全股交易條款,瑞信股東將以22.48股瑞信股票獲得1股瑞銀股票,相當于每股0.76瑞士法郎,總對價為30億瑞士法郎。
由于該收購涉及瑞士金融業兩大支柱,且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間的第一宗合并交易,被市場認為是2008年來歐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一樁銀行業收購案。
無獨有偶。在大西洋彼岸,掀起此輪歐美銀行業風暴的硅谷銀行,其命運也以被收購告終。當地時間3月27日,美國第一公民銀行宣布,已與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簽署協議,以164.5億美元的折價購得約1100億美元硅谷銀行資產,這些資產涉及其存貸款、其他資產及負債。
這成為近年來歐美金融市場少有的動蕩時刻。這也不免讓人想起美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儲貸危機,彼時由于美聯儲激進加息,導致大量中小銀行破產。但更深的記憶還是來自15年前的次貸危機——當時美國按揭貸款和相關衍生的損失引發了資金緊縮,使美國和歐洲多家銀行倒閉,并迫使政府出面救助。
“回想起當年的金融危機,感覺就像末日來臨前一樣。”曾親歷多次金融危機的資深交易員、灰巖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創始人廖聞鍇對《財經》記者回憶道,“不過,經歷次數多了,自己心態也變得淡定了許多。現在回頭來看,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些危機不過都是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一個節點。”
金融服務巨頭DeVere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尼格爾·格林(Nigel Green)也對《財經》記者表示,全球主要股票市場的波動加劇是由對全球銀行系統的擔憂引發的。但與此同時,它也將被投資者視作買入的機會。
這一次廖聞鍇的確抓住了機會。“當前市場波動是由恐慌情緒驅動的,那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就有可能成為風暴眼。”他說道,“在瑞信風波爆發前,我就做空了德意志銀行(下稱“德銀”)在美國市場的股票,因為與前者相似,近年來德銀有諸多不利的市場傳聞。不過,我也沒有做空特別多,因為現在市場上可供出借做空的頭寸不多了。”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歐美多家銀行已被收購,但這并不意味著歐美銀行業風暴偃旗息鼓,其一大風險就是美國金融體系將因此收緊對美國家庭和企業的貸款,以確保資產負債表健康。這帶來的外溢效應將十分顯著,因為這將抑制美國對其他國家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同時也將使股票和其他資產價格下降。
富蘭克林鄧普頓研究院主管及首席市場策略師斯蒂芬·多夫(Stephen Dove)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認為,硅谷銀行倒閉的影響將繼續令整個全球銀行業承壓。一方面,隨著監管機構重新評估現有的資本、流動性風險框架,美國地區性銀行可能面臨更高的運營成本。另一方面,為尋求更大投資回報,目前現金存款仍從銀行轉移到貨幣市場基金。“信貸供應不足可能開始對消費者支出產生負面影響。不過,目前銀行業資金、流動性和資本狀況總體較好,不能將當前危機與2008年時期相提并論。”他說。
截至《財經》記者發稿,市場對歐美銀行業危機全面蔓延的擔憂逐步減退。當地時間3月30日收盤,美股全線漲超1%,收復硅谷銀行倒閉以來跌幅。次日,美股三大指數續延漲勢。
不過,目前市場對歐美銀行業風波的擔憂逐步轉移到實體經濟上。花旗表示,如果對銀行狀況的擔憂持續更長時間,導致資金成本和融資環境變得緊張,信貸增長可能會停滯,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可能放緩至1.6%。
量寬轉向與冒險游戲
近期市場所有的動蕩都始于幾周前硅谷銀行的擠兌風波。當地時間3月9日,受存款擠兌影響,硅谷銀行股價重挫60%。僅一日后,硅谷銀行宣告倒閉,成為美國史上第二大銀行破產案。不僅如此,這也帶動了銀門銀行等多家美國中小銀行相繼破產。
風暴席卷而來,這讓全球投資者開始狙擊金融系統的薄弱環節。不久后,排在問題清單前位的瑞信成為又一家倒下的銀行。當地時間3月15日,瑞信五年期信用違約掉期(CDS)上升近100%,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3倍。同日,瑞信股價一度暴跌30%。
上述銀行倒下的原因均源自于流動性問題。當地時間3月9日,客戶一日從硅谷銀行提走了420億美元。截至當天營業結束時,該行的現金余額約為負10億美元。當時,硅谷銀行的團隊還試圖重建資產負債表。“但我們并沒有成功,時間和環境并沒有站在我們這邊。”硅谷銀行員工在回想該行最后幾小時經歷時表示。
瑞信也上演著相似的劇本。在股價重挫前一周,瑞信面臨每天高達100億美元的客戶資金流出。不僅如此,瑞信還失去了大股東的支持。瑞信最大投資者沙特國家銀行(Saudi National Bank)的原董事長阿馬爾·胡代里(Ammar Al Khudairy)在利雅得舉行的一個金融會議上表示,由于Saudi National Bank已持有瑞信9.9%的股份,便不會再對瑞信有更多投資。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一些歐美銀行而言,其實危機的種子早已埋下。以瑞信為例,近年來,該行每年面臨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虧損。去年秋天,在瑞信健康狀況引爆網絡輿論之際,客戶從該行抽走了1200億美元。
在沈建光看來,之所以歐美銀行會出現流動性問題,一大原因在于美聯儲、歐央行貨幣政策從極度寬松到劇烈緊縮的大轉換,這對美國銀行業和金融穩定形成沖擊;另一原因則在于儲戶不信任銀行了,這使信任危機和流動性危機疊加到一起,由此形成了負反饋。
“為應對流動性問題,硅谷銀行被迫出售債券。受美聯儲加息影響,債券資產價值降低,硅谷銀行因此損失較大。損失兌現牽動了儲戶神經,引發了市場擠兌,反過來又加大銀行拋售債券壓力,使資產進一步縮水。”他解釋稱。
經歷了量化寬松時代以及疫情時期極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后,美聯儲于去年3月開始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快步伐的加息,去年一年累計加息425個基點。這導致全球“便宜錢”減少甚至消失。截至目前,全球負利率債券從2020年底高峰的18萬億美元降至當前的1.2萬億美元,且剩下的全部是日本債券。在此背景下,2022年,美國市場形成了罕見的“股債雙殺”局面。
“作為中央銀行,美聯儲的政策目標也是多重的,要控制通脹,穩定就業,還要保持金融穩定。但這些目標有時是互為矛盾的,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美聯儲的行為便有些顧此失彼,這使利率風險不斷蔓延。”沈建光表示。
此前,美聯儲曾要求銀行在壓力測試中展示它們將如何受到通脹上升的影響。但這種情況是通脹達到近期峰值后才發布的,而測試的結果則顯示,這不會對銀行的運營產生任何實際影響。
“不過,這也不能只怪美聯儲,其實無論是硅谷銀行,還是其他市場參與者,有些行為確實有些冒險了。”廖聞鍇表示,“在硅谷銀行破產前,市場其實就已經開始討論降息了,市場敢于與美聯儲背道而馳。這背后的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監管逐漸放寬,市場犯錯的成本變低了。”
在去年二季度的業績報告中,硅谷銀行便告訴投資者,該行正將業務重點轉移到管理降息敏感性上。而這并非孤例。2022年10月以來,市場一直與美聯儲對抗。據媒體彭博提供的金融環境指數顯示,市場正持續走向寬松。在今年初,市場一大熱門交易便是押注美聯儲降息,美債價格將從低點大幅反彈。
近年來,美國對金融監管更為放松。201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了一項新法案,資產規模低于2500億美元的銀行無需通過美聯儲的年度壓力測試,也不必向其提交有關破產后如何清算的“生前遺囑”。在某種程度上,這刺激了銀行業更多“冒險游戲”。
監管的果斷與糾結
相較于雷曼危機時期,此次歐美監管機構的反應更快也更全面。無論是處理硅谷銀行破產,還是推動瑞銀收購瑞信,美國和瑞士監管機構都是趕在周一亞太市場開盤前敲定。從決策到執行,用時不過幾日。
為撮合交易,監管機構頗為慷慨和果斷。瑞士監管機構提供了1000億美元的流動性額度,對一些資產提供了超過90億美元兜底,并為瑞銀增資提供了較長的寬限期。不僅如此,它們還創設了幾個先例:首先,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交易在沒有股東投票的情況下通過;其次,提供了反壟斷豁免權;再次,對172億美元的瑞信AT1債券全面減記。
其中,AT1債券全面減記一度在市場上掀起軒然大波。3月20日早盤,一些亞洲銀行的AT1債券出現創紀錄跌幅。當日開盤后,香港東亞銀行(Bank of East Asia)票面利率為5.825%的永續美元債價格下跌8.6美分至79.7美分。同日,景順AT1資本債券ETF(Invesco AT1 Capital Bond UCITS ETF)大跌13.61%。
投資機構晨星戰略顧問陳鵬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道,之所以AT1市場波動劇烈,是因為瑞士政府的意外之舉,讓市場懷疑這將導致這一規模高達2500億美元的市場被重新定價。
“根據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資本清償順序的相關規定,最先被清償的資本為普通股權一級資本,其次便是AT1資本和Tier2資本。但在此次瑞銀收購瑞信過程中,清償順序靠前的普通股東權益受到了一定程度保護,而相對更加安全的AT1卻反而被全額減記,這與上述規定的清償順序相悖。對于債券投資者來說,如果得不到收益,那就只能全賠了,這是0和1的事情,沒有中間選項。”他說。
據瑞銀董事長凱勒赫(Colm Kelleher)回憶,瑞信股價暴跌后,他就接到了瑞士官員的電話,這些官員來自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瑞士央行和財政部。他們傳遞的信息很明確,瑞銀將接管瑞信,否則后者將破產,這可能會連累瑞銀和其他銀行。凱勒赫給瑞士財長凱勒·薩特(Karin Keller-Sutter)打了個電話。他被告知“這是唯一的選項”,然后對方就掛斷了電話。
在沈建光看來,之所以歐美監管機構反應迅速,還是因為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吸取了教訓。雖然自此之后,歐美政府一直強調不會救市,但當它們不得不這樣做時,它們還是會出手。
花旗集團前全球外匯主管、深數宏觀(DeepMacro)聯合創始人兼CEO(首席執行官)杰弗瑞·楊(Jeffrey Young)對《財經》記者說,盡管這次銀行危機的潛在問題看起來要小得多,但與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3月疫情時采取行動相比,全球央行這次在采取行動之前的“認知差距”幾乎為零。這表明央行對流動性供應的態度是“不冒險”,可能是因為認識到流動性枯竭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在典型的認知差距期間市場反應有多糟糕。
凱勒·薩特便于近日坦言,“什么都不做”不是一種選擇,無序破產將把其他銀行推入深淵,并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在投資者信心危機中,已然無法挺過另一天的交易了。凱勒·薩特還援引數據估計,無序破產的影響可能高達瑞士經濟產出的2倍。
同樣出手的亦有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在危機爆發后,美國和英國的監管機構致電瑞士同行,以確保它們不會讓瑞信拖垮全球市場。
不過,雖然救市行動相對較快,但這不意味著監管機構沒有糾結。在風險事件暴露后,美聯儲等機構在抗通脹之外又多了一層任務,這使其要在抗通脹和防風險間“走鋼絲”。
在硅谷銀行風波后的首次議息會議上,美聯儲仍加息25個基點,并暗示降息將不會很快到來。在危機前,市場的一致預期是,美聯儲將加息50個基點。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美聯儲的確曾考慮過暫停加息。“之所以對加息達成非常強烈的共識,還是因為通脹和勞動力市場的數據最近強于預期。”他說,“美國的銀行體系健全且富有彈性。現在確定(風險事件)影響程度還為時過早。”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月美國新增非農就業人口31.1萬,較前值50.4萬大幅回落。薪資方面,員工平均時薪環比上漲0.2%。這說明美國勞動力供給仍然不足,工資通脹仍有支撐。
此外,與2008年次貸危機前空置率畸高完全不同,目前美國的住房空置率和租房空置率均處于歷史低位。這意味著,美國房價和租金的彈性也可能較以前增加,進而使得整體通脹的韌性更強。
誰是下一個?
目前,尚不得知這場危機還要發酵多久,但市場已然成為驚弓之鳥。最新一例是,當地時間3月24日,受瑞信AT1債券全面減記影響,德國最大貸款機構——德銀股價盤中一度下跌15%。隨后雖收復一些失地,但截至當日收盤仍下挫8.53%。3月迄今,德銀市值一度蒸發超四分之一。
此外,觸發歐美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存款流出問題仍在持續。美聯儲當地時間2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到截至3月15日的一周時間里,美國銀行存款總共流失近1000億美元,達到了984億美元。其中,小型銀行的存款總額流失1200億美元,而大型銀行的存款總額則有所增加。
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分析師劉勁津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近日金融市場風險事件頻發,但從宏觀層面來看,目前歐美銀行業風險暴露的可能性不會太大。其原因在于,其銀行業杠桿率更低,資本充足率更高。
中金公司也在最新研報中表達了類似看法。該機構稱,融資成本上升帶來的經濟下行甚至衰退、流動性沖擊和債務危機是三種層級的壓力。當前美國正處于流動性沖擊時期,而流動性壓力轉化為大規模的債務壓力通常需要高杠桿和央行干預不及時兩個條件的觸發。由于當前全美宏觀杠桿率在經歷了次貸危機去杠桿后仍處于健康水平,這意味著未來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較低。
市場研究機構Haver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美國金融機構杠桿率已從2008年時的123%回落至75%左右。美聯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2月,美國全部本地銀行貸存比達67.5%,低于2019年底76.4%的水平。另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測算,即便按考慮到未兌現損失后的mart-to-market來計算銀行資產,除兩家外,目前幾乎其他所有的銀行都有足夠資產支付其未被FDIC擔保的存款。
在歐洲方向,平安證券則在最新研報中稱,雖然當前歐洲銀行業承受一定壓力,但主要指標仍好于2019年水平,更好于2016年以前的水平。這意味著,雖然瑞信、德銀處于“風暴眼”之中,但歐洲銀行業非“將傾之大廈”。
歐央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歐元區銀行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CET1)為14.74%,高于2019年三季度0.37個百分點。同期,歐元區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大幅降至1.79%,不良貸款總額也降至3450億歐元。這說明歐元區銀行業資本充足率仍然較高,且不良貸款率仍處低位。
不過,沈建光仍提醒,雖然整體來看,歐美銀行業風險情況相對可控,但從細分領域來看,美國中小銀行及商業地產都是薄弱環節。他認為,對中小銀行而言,其資產充足率整體不及大銀行,且其商業地產貸款等結構性業務風險更大。此外,由于債務規模較大,美國房地產行業和相關的金融業務不久也將迎來風險大考。
據NBER測算,目前美國大型非系統重要性銀行減值比例為10%,小型銀行為9.1%。相較而言,系統重要性銀行減值比例則為4.6%。此外,美國小銀行商業地產按揭貸款占貸款比例44%,對比大銀行的這一比例為12.9%。這意味著,前者資產減值壓力將更大。
研究機構明晟(MSCI)Real Assets的統計數據顯示,僅今明兩年,美國商業地產就有近萬億美元債務到期。該機構認為,受風險事件影響,放貸機構可能將收縮貸款規模。同時,在加息環境中,更高的借貸成本和下跌的房產價值將增加商業物業持有人再融資難度。因此,商業房地產債務壓力陡增,并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
不僅如此,風險外溢,受損的不只是金融產業。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監管者對于金融機構的風控援手,將帶來一連串的外溢效應——家庭和企業貸款收緊、外貿商品與服務需求壓抑、股票和其他資產價格下降。
康奈爾大學的貿易政策和經濟學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便稱,目前對全球經濟來說可能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時刻。在發達經濟體利率上升基礎上疊加銀行業的問題,其影響可能波及全球。
在陳鵬看來,這背后主要的傳導渠道仍是美國貨幣政策。受美聯儲加息影響,美國金融環境收緊,使得借貸成本上升,進而影響美國企業和居民需求。由于美國是全球的貿易逆差大國,這將抑制美國對中國等國生產的電子產品以及旅游業等服務貿易的需求。
他進一步表示,全球金融體系也是以美元為基礎的。美聯儲不斷加息疊加風險事件頻發,將影響其他經濟體的美元融資成本。這將可能會收緊對國內家庭和企業的貸款,從而放大美國進口疲軟對這些國家的沖擊。
花旗認為,如果銀行用更積極行動削減賬面上的風險資產,全球經濟增長將進一步下降,或降至1.5%。如果以美國和歐洲多家銀行倒閉為特征的全面危機發酵,將導致全球經濟萎縮,降幅可能高達2%。
醞釀新一輪監管變革
在危機稍緩片刻,無論是市場還是監管機構,大家都在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沒有提前預料到硅谷銀行的風險?直到2022年底,監管機構才警告硅谷銀行,利率已大幅上升,其利率風險模型并不充分。除此之外,監管機構也沒有意識到,銀行存款流失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
“我們在(事發)第一周都在問自己的問題是,‘這是怎么發生的?’”鮑威爾說道。
美聯儲金融監管副主席巴爾(Michael Barr)則表示,他于2月中旬,也就是硅谷銀行倒閉幾周前,才了解到硅谷銀行存在與利率風險的相關問題。
對此,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坦言,監管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快速做出決策的地步。它關注的是一致性而不是速度,“在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系統的設計不足以強制快速改變”。
“(監管)運行的速度??與我們過去看到的非常不同。”鮑威爾也說道。
實際上,監管決策速度較慢的問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彼時,美國跨州銀行業務的壁壘逐步減少,美國聯邦監管機構試圖將跨州的規則正式化,華盛頓方面由此獲得了更多的決策權。經過幾十年的演變,這也使得美國銀行監管的優先級從速度向一致性、公平性和透明度轉變。
此外,在沈建光看來,科技的發展也為銀行業及監管帶來挑戰。與2008年不同的是,當前這些銀行資金外流的情況表明,數字銀行業務使客戶更容易將資金撤出,同時社交網絡更可能放大損失。
如果從瑞信去年秋天和今年3月的兩次流動性危機來看,其流動性問題都與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聞有關。最終,這些傳聞如滾雪球般演變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對于硅谷銀行來說,在遭遇存款擠兌風波時,“硅谷銀行遭遇危機,甚至可能會破產”的傳聞亦如雪片般散落在美國西海岸、東海岸,甚至中國的創投圈。
“現在操作都很方便,只需要手機一點就可以把錢從硅谷銀行取出來了。”一位在硅谷的創投人對《財經》記者表示,“回想硅谷銀行破產的那幾天,社交媒體擴散的恐慌情緒,的確是推動事態發展的加速器。”
對于上述情況帶來的挑戰,鮑威爾近日表示,這確實表明需要對監管采取可能的變革。“監管需要跟上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他說。
當地時間3月28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就美國區域銀行倒閉事件舉行的首場聽證會上,巴爾暗示將加強監管。他建議,有必要對資產超過1000億美元的銀行施加更為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標準,美聯儲將通過多種情景加強對銀行的壓力測試,并向大銀行提出長期債務要求。
白宮也于3月30日提議,收緊對中型銀行監管,增加壓力測試頻率。白宮還在聲明中表示,這些措施不需要得到國會批準。
標簽: